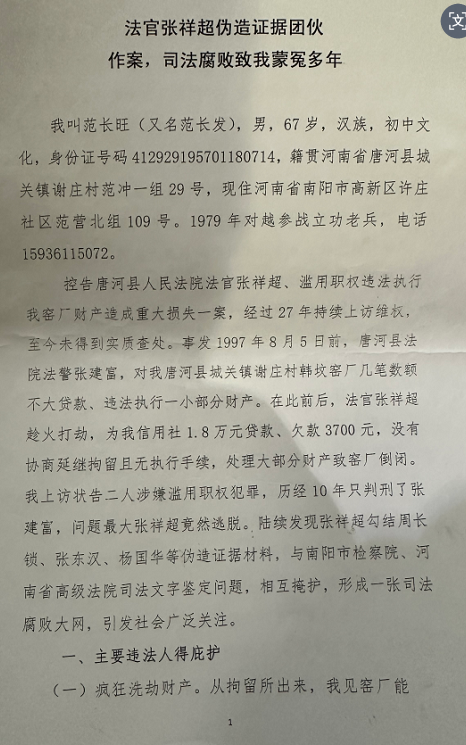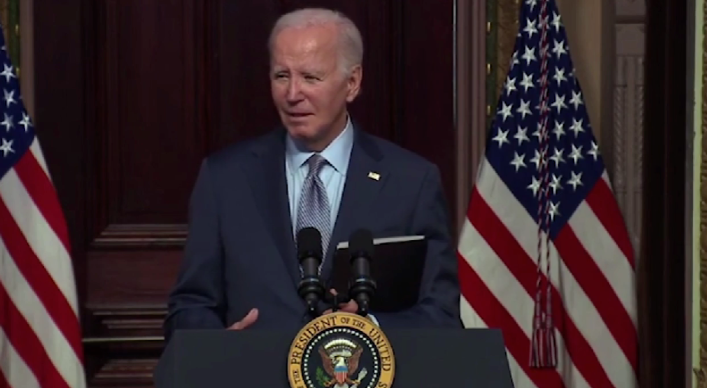《帝国边缘》是哈佛大学教授马娅·亚桑诺夫2005年的著作,她以生动细致的笔触,讲述了在大英帝国的印度、埃及边疆收藏历史文物的收藏家的故事。
恰如书名所示,该书的故事是在“帝国边缘”展开:时间上,1750-1850年是大英帝国从偏居一隅的大西洋岛国发展壮大的一百年,其时英国主宰的全球规则尚未确定;空间上,则是站在宗主国边缘人民和地区的立场,从收藏家的角度来看待英、法殖民帝国与东方的印度、埃及的历史交往与文化碰撞。
亚桑诺夫认为,在殖民帝国扩张的历程中,权力与文化混乱地交汇融合,大英帝国本身成为一种“收藏”,同样被复杂的东方力量所塑造和改变。
撰稿丨刘军
以克莱武为代表的帝国收藏家
《帝国边缘》一书按照时间顺序,把英国将印度和埃及收入它的东方帝国的过程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开始,详述了18世纪末期征服印度的历史,主要讲述了英国著名的殖民军统帅罗伯特·克莱武的军事、政治经历和收藏家的生涯。第二部分是大英帝国收藏的关键时期: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1799年英国占领南印度的塞林伽巴丹,英国逐渐开始在东方和美洲直接对抗法国的殖民扩张,大英帝国的政策转向主动征服,沿着印度的前线和边界“收藏”领地。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英法两国19世纪上半期在埃及的争霸战争和“收藏竞赛”,英法两国为在埃及扩大政治影响而对抗,引发了搜罗文物的“暗战”。
其中,克莱武的故事颇具代表性和戏剧性。1757年,罗伯特·克莱武指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私有军队”
(由欧洲士兵和印度土兵组成)
,在普拉西打败了孟加拉的纳瓦卜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确立了军事优势,并以东印度公司的傀儡取而代之,瓦解了莫卧儿帝国在孟加拉的权力结构。普拉西大捷开启了影响英国全球地位的一系列事件。1765年,莫卧儿皇帝授予东印度公司顾问的地位,可以在孟加拉行使征税权。从此,东印度公司除了是个拥有英王特许状的私有商业机构外,还开始在印度承担了部分国家职能。罗伯特·克莱武(1725-1774)集冒险家、军事家、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曾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他被英国人认为是大英帝国最伟大的缔造者之一,而在殖民地人民眼中却是罪恶的强盗。
从此,大英帝国开始了在印度的收藏史,不仅“收藏”权力和领土,开启了大英帝国的海外建设,逐渐变成全球的统治者;同时,也收藏聚敛大量财富和珍宝。克莱武成为英属印度的帝国收藏家,他回到英国后,通过贿选获得上议院议席,此后还被任命为驻印英军总司令。但是,英国公众质疑东印度公司贪婪掠夺的声浪不断高涨,克莱武成为众矢之的。1772年,克莱武在国会受到政敌公开指控,指他非法聚敛财富,令国家蒙羞。不过,克莱武的辩才起了作用,最后全身而退,荣誉和财富都完好无损。
尽管得到国会的赦免,克莱武的抑郁症却加重,1774年自杀身亡。但克莱武家族的故事并没有结束。1798年,他的儿子爱德华·克莱武亲自前往印度,作为马德拉斯总督服务了五年。在那里,他和家人又一次成为印度的收藏家,充满激情地收集印度艺术品。
英法帝国的文物收藏“暗战”
亚桑诺夫笔下的帝国收藏家,有拿破仑·波拿巴和罗伯特·克莱武这样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有英国外交官亨利·索尔特,他好不容易谋到了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官差,希望拿到养老金安享晚年;有离经叛道的欧洲军人查尔斯·斯图尔特,他在印度娶妻生子,收藏文物,是以往的帝国历史中不会关注的无名之辈;还有印度土邦迈索尔的土著王公蒂普苏丹,他周旋于英法帝国之间,小心翼翼地扩张自己的领土和权力。
其中,英国驻埃及领事索尔特和法国驻埃及领事德罗韦蒂在埃及进行的文物收藏竞争的“暗战”,最终导致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收藏了大量的埃及文物,是书中颇具典型性的故事。
索尔特1780年生于英国的利奇菲尔德。早年学画,成为英国贵族瓦伦西亚子爵的随员,陪伴子爵前往东方旅行,到达了好望角、印度和红海地区。他画了这些地区的插图出版,渐渐知名而成为业余的“东方学家”。1815年,索尔特被瓦伦西亚推荐,担任英帝国驻埃及总领事,开始在埃及搜罗文物和手工艺品。
《帝国边缘》,(美)马娅·亚桑诺夫 著,索·恩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版。
索尔特赞助了在底比斯和阿布辛贝地区的发掘工作,亲自对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进行了重要的考古研究,他破译象形文字的能力赢得了法国著名的埃及学家、象形文字的破译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的赞赏。
不过,他搜罗文物的工作,遭到德罗韦蒂的竞争和阻挠。德罗韦蒂对埃及有更全面的了解,同阿里帕夏的关系也很好。但是索尔特得到了意大利人贝尔佐尼和希腊人阿塔纳西的帮助,在这场文物收藏竞赛中胜出,在短短两年之后,就开始出售他收集的文物和工艺品。索尔特于1827年去世,享年47岁。今天,他收集的埃及文物和手工艺品还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
边缘人物与边缘帝国的自我塑造
亚桑诺夫认为,这些活跃于“帝国边缘”的文物收藏家们,其实是帝国权力体系中的边缘人物,都需要用收藏品来重塑自己的形象。
法语有口音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把占领埃及、“收集领土”看作是通往法国权力顶层的阶梯——他也的确从埃及回军巴黎,成就了自己的帝王霸业。克莱武本是英国权力体制的局外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收藏,立志要赢得英国权势阶层的接纳。索尔特、斯图尔特等人,更是起自寒微,通过文物收藏而在大英帝国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一席之地。
他们都是收藏家——既是比喻意义上的收藏家,因为他们是领土和权力的征服者;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因为他们在征服领土之后,系统地获取文物:拿破仑把国家资助的收藏提高到新的水平;蒂普苏丹建立了大型图书室和塞满了欧洲物品的宝库。英法帝国在东方的征服使得两种“收藏”合二为一:占领领土和侵占物品。
大英帝国在与法国争霸的过程中,也逐渐从偏居“全球边缘”的大西洋贸易小国,逐渐将自身塑造成全球帝国。在印度、埃及这样的帝国边缘地带进行的收藏活动,是这些历史人物的自我塑造之道,也是大英帝国的自我塑造之道。从1750年到1850年,英国在印度、埃及等地区“收藏”出了一个东方帝国。到1850年,大英帝国通过征服和直接统治逾百万外国臣民而形成了洲际帝国。
《自由的流亡者》,(美)马娅·亚桑诺夫 著,马睿 译,索·恩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版。
亚桑诺夫在书中总结说,她无意为大英帝国进行宣传或道歉。她只是希望这段历史能够使人们看到“成功的国际关系中的基本人性”,并且做到互相“借鉴、学习、适应和给予”。帝国收藏家的故事显示,文化遭遇的过程要比“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历史对抗复杂得多,足以抵消当代“东方学”历史叙述中的“一边倒”倾向:帝国主义并非单向街,在试图理解欧洲势力如何压迫、改变东方国家时,东方也改变和重塑了欧洲帝国。
当然,对于亚桑诺夫的“帝国史观”,欧美史学界不乏批评的声音。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苏维尔·卡尔指出,亚桑诺夫认为历史学家可以把大英帝国看作是具有“成功的国际关系中的基本人性”的例证,这一点绝不敢苟同。在殖民扩张过程中,欧洲人可以与被殖民者交朋友,发生性关系,甚至结婚生子,有些欧洲人还会对欧洲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和剥削感到愤怒和痛苦,但这并不能构成对殖民主义帝国历史的系统重估。
在批评家理查德·戈特看来,亚桑诺夫颠倒黑白,“无视历史的本质”。他认为,大英帝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大规模的希特勒计划”,充满着军事征服、种族灭绝、戒严法和“特别法庭”、奴隶制和强迫劳动,以及集中营——在评价大英帝国时,这一立场“必须是主导地位”。
当然,对于亚桑诺夫来说,戈特这种将大英帝国与希特勒纳粹德国混为一谈的“本质主义”的激进立场,不仅老套过时,而且必定会挑起新的“历史战争”。在“成功的国际关系的基本人性”与“纳粹版大英帝国”之间,历史叙述的鸿沟如此巨大、显豁,表明有关大英帝国的历史辩难,还会持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