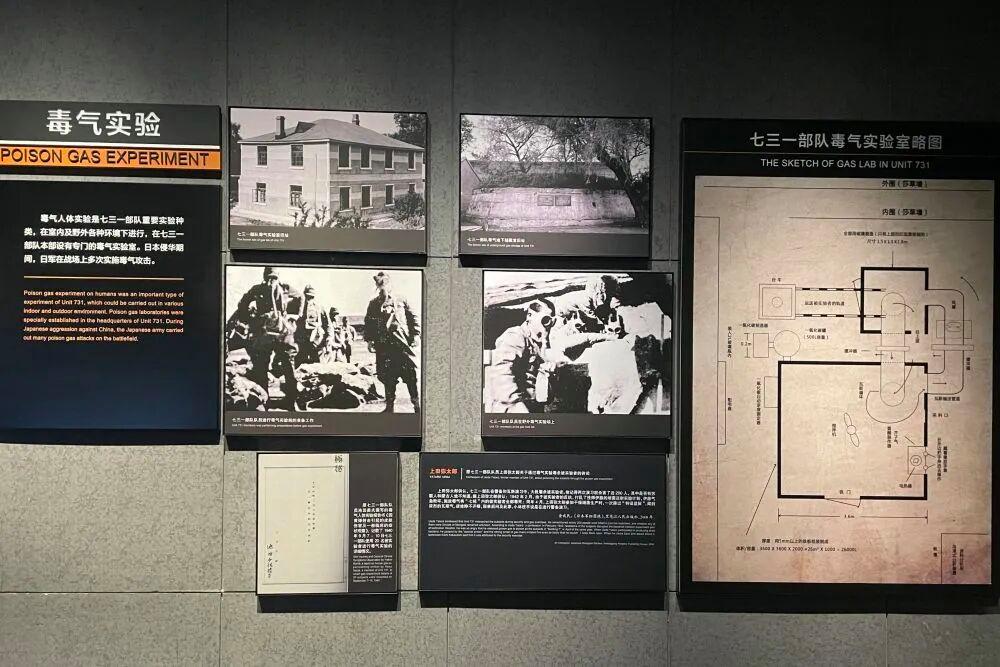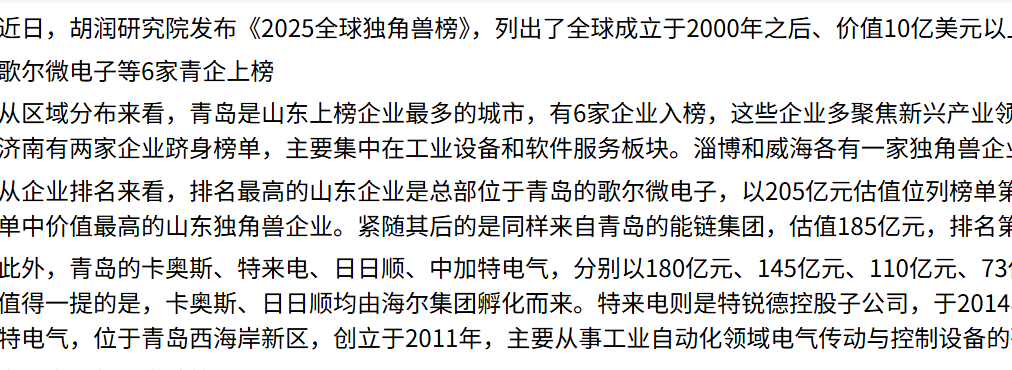原标题:返乡扶贫的“95后”:“5+2,白+黑”,每天都是“跑”着过的
陈程刚结束村里“春晚”的表演,脸上厚重的舞台妆还没来得及卸掉。这也是她的工作之一。“我们办公室出的节目是打快板。”
她从兜里掏出手机,密密麻麻几十行台词里,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是“脱贫”。

2018年跨年时,陈程的几个好朋友不是在香港看演唱会,就是去了北极看极光。只有她,在家里守着电视遥控器,在不同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之间来回切换。“朋友圈也懒得发了,画风都差不多。”
我的好友陈程是广西灌阳县灌阳镇的一名公务员,从事精准扶贫工作。那里是我们的家乡。从桂林市区到镇上只有大巴,汽车在前两年刚建成的高速公路上摇摇晃晃两个多小时,绕过无数个弯,才能开到山的深处。灌阳镇就藏在这崇山峻岭之中。
上中学时,陈程梦想成为一名翻译官。像经常出现在总理记者见面会上的张璐那样,衣着大方干练,梳一头一丝不苟的短发,唇齿张合之间,就能迅速而精准地把每一句中文译成英语,“感觉这样特别酷。”
但去年6月30日,她从河南郑州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坐上回家大巴,山一座接一座地从窗边掠过,路的前方也只能望到层层叠叠的山。深浅不一的绿向四面八方绵延开来,没有尽头。
她的人生又一次和故土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第一次离农村这么近
陈程从小在县城长大,家境不错,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除了偶尔去一下乡下的外婆家外,她人生中前二十年和农村的交集微乎其微。
“我那时觉得农村就像陶渊明写得那样,很田园的感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用来享受的。”
直到去年10月,陈程以镇扶贫办工作人员的身份下乡,见到了贫困户张文军(化名)和他的妻子。
张文军家远离村落,孤零零立在半山腰。通往他家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道,对面不远处就是“山洪灾害危险区”。
房子虽然是两层的砖混结构,但没有安玻璃窗,砖墙也被腐蚀成了灰褐色。从空洞的窗口望进去,黑漆漆的一片,依稀可以看到内墙只用水泥粗略地抹了一遍。横梁裸露着,除了施工用的木质脚手架,空无一物。
陈程和同事来到张文军家时,张和妻子正坐在门口,一人一张小板凳,谁也不说话,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他们坐在那里,已经和这个社会彻底脱节。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联。”

张文军快六十了,背佝偻着,两鬓斑白,平时会去镇上做点儿零工,儿子在外地打工,妻子则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家里的年收入加起来不会超过两千块。
陈程突然发现,不是每个农民都能过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还有不少人像张文军这样活着。她第一次和农村离得这么近。
不下乡时,陈程还要接待因为各种事务来扶贫办反映情况的人,每天至少七八个。她要耐心解答他们的各类问题,大多数人通情达理,但偶尔也会遇上一两个例外。
一次,一名中年男子冲进办公室,大声质问自家为什么没被评上贫困户。陈程说,因为他享受了五保政策,不在贫困户的评选范围。陈程和同事们花了很长时间向他解释,可无济于事。他始终气势汹汹地叫嚷,连办公室里气场最强的王姐都镇不住。
“他还要把我的电脑搬去卖钱。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通知保安把他架走了。”陈程苦笑着摇摇头。
“每天都是‘跑’着过”
或许因为父母也是公务员的缘故,陈程从小就喜欢安定的、可掌控的东西,不希望生活里有太多变数。
以前上大学时,她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四点一线,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准时上床睡觉。
选择考公务员也是看中它的稳定可控,喜欢这种朝九晚五的感觉。但事实却和陈程的想象全然不同,“5+2,白+黑”才是生活的常态。
成为职场新人的第四天,她就加班到了晚上十一点。饿着肚子走出办公室后,直奔附近的夜宵摊,点了炒粉和烧烤。那时,她以为十一点已是加班的极限,完全没想到之后还会熬大夜。最夸张的一次,她连续三天没合过眼。
“每天都是‘跑着’过的,”陈程说,“包括我们领导,你能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跑’。如果你不跑,做事慢吞吞的,就跟不上节奏。”
如今,陈程的办公桌在镇政府政务中心三楼最里侧的房间。这间二十余平米的办公室内整整齐齐摆放着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以及一摞摞堆叠在一起的文件。
陈程从小山般的纸堆中抽出一个厚厚的绿皮本子,封皮上写着“工作日记”。短短半年内,她已经记完了一整本。

本子里是她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从最简单的打印、复印文件,到填写、核查各类表册信息,再到下乡去贫困户家里调研,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走访了23户贫困户。琐碎繁杂的事务,把每一天填得满满当当。
因为工作繁忙,镇政府又没有食堂,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程只能吃快餐过活,索然无味,又没有营养。她开始怀念起学校食堂,尤其是美味的河南烩面和月亮馍。
腊月二十七,陈程匆匆赶来和我见面。
她刚结束镇里“春晚”的表演,脸上厚重的舞台妆还没来得及卸掉。这也是她的工作之一。“最近都忙着排练,我们办公室出的节目是打快板。”
她从兜里掏出手机,密密麻麻几十行台词里,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是“脱贫”。
过去,“精准扶贫”是陈程在新闻里才会看到的词汇。现在,她每天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精准扶贫,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精准到户、精准施策、精准到人。”
为了做到“精准”二字,这两年贫困户的评议流程中特别加入了村民小组、村委会评议环节,以保证贫困户申请人的家庭情况真实可信。
“至少能切实地帮到别人”
春节前夕,这座偏远的南方小镇异常温暖,日均最高气温达到了20度。按县里的规定,过年前,陈程要去对口帮扶的贫困户李小春家慰问。一箱牛奶,一箱苹果,是慰问的“标配”。
工作半年,陈程早有了自己的下乡“标配”:一个黑色单肩包,一辆白色电动车。她麻利地把慰问物资往车前的脚踏板上一放,跨了上去,风风火火地往村里骑。
刚进家门,李小春的妻子唐玉凤(化名)便热情地迎了上来。他们住在一间颇有年代感的平房里,这间房兼具了卧室、客厅、厨房三重属性,床、沙发、电冰箱统统挤在一起。
陈程和唐玉凤聊得起劲,嗑起了瓜子。唐玉凤告诉她,家中新添置了电冰箱、液晶屏电视机,儿子学会了砌墙的手艺,孙女蹦蹦跳跳地上了小学,小女儿也即将迈入高中的大门。
陈程觉得欣慰,对工作的满意度又高了一些。这份工作虽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轻松,但至少能切实地帮助到别人,而且很稳定。
二十多年来,陈程的梦想从老师变成翻译官,又从翻译官变成公务员。唯一不变的,就是她对稳定生活的向往。她甚至不愿意去企业工作,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炒鱿鱼。”
我俩共同的一位好友,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去了成都工作,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工作了两三个月,又辞职做了独立编导,自己接活儿干。“我真的蛮佩服她的,但我可能过不来那样的生活,看着她奔波来奔波去,我觉得安安稳稳地在小县城也挺好。”
过去的一年,县里建成了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座大型购物商场,横贯它的江河上架起了一座在当地颇为雄伟的大桥,移动支付悄然出现在沿街的商铺里、街边的小摊上……

陈程见证了所有的变化,看着日子一天天变好,但偶尔还会怀念城市的丰富多彩。
前两年国庆假期,陈程和我还有两位好友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住在淮海中路附近,短短几天里,我们体会到了这座城市的所有风情,每个人都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
尤其是陈程,聊天时动不动就会来一句,“要是能再去一次上海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机会去上海工作,你会干什么?”我问她。
“考公务员。”陈程毫不迟疑。
小时候,电视机里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长大了,慢慢明白,走得到的地方是远方,回得去的地方是故乡。
离故乡越来越近,“年味儿”才越来越浓。故乡那层层叠叠的烟火、蜿蜒曲折的小路、熟悉的菜香,甚至偶起的几声犬吠,都是辞旧迎新的标配。我们离开故乡在外打拼,回乡的期待却不曾停歇。
2018年伊始,我们再一次凝望故乡。在那里,8年留学生度过了归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大龄女人生下了二胎女儿,一个即将消失的村落拍下了一张全村福……
我们试图呈现中国版图上不同风貌的故乡,从一个个故事里勾勒大变革时代的微观图景、寻找故乡给予新时代奋进者的给养。我们记录他们的故事,也是记录社会发展的印痕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