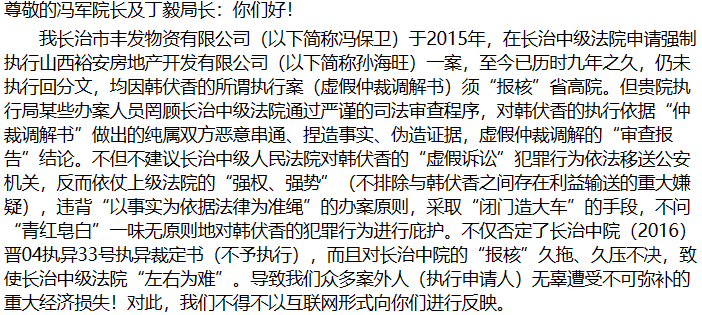一份“神秘”的名单
维权之路竟然由一起偶然的事件引发。
4月份,徐瑞宝找到他以前做过事的一个老板,要求对方出钱给他治病。这个老板最后给了他10万元。
消息传到耒阳老家,已回到家乡养病的患病村民似乎受到启发。而在此前,村里有死者的亲人去深圳找过相关爆破公司,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年已拿了工资了。追讨补偿一事不了了之,没有人去研究法律。
5月22日,徐瑞乃、谷运成、刘洪云等10名病情严重的村民从耒阳老家赶到深圳,当天下午,找到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爆破公司要求补偿。这家公司在表示同情的同时表态说,口说无凭,他们需要去鉴定以确定是否是职业病,如果是,就赔。
消息再次传到耒阳,更多的人陆陆续续前往深圳,至6月初,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
6月12日,徐瑞宝去医院问结果,被告知6月1日前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了,6月15日可取。
“事实上,在去医院取结果之前,我们都知道了检查结果”,徐瑞宝说,一份名单已被患病村民从乡里得知。他们被告知,名单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到耒阳的。
这份名单是《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名单中的150人全部是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过检查的。150人的胸片结果以Ⅰ、Ⅲ、㈠、0或者“复查”表示。这些不同的数字符号代表患病的程度或者没有患病。
正是这份名单,引发了一场风波。
6月15日,不少村民又从耒阳赶到深圳,去医院拿检查结果。而在医院出具的“放射科报告书”中,患病人群并没有被确诊为尘肺病,大多是“发现阴影”、“复查”、“作进一步诊断”。
“有的人快死了,还说要复诊?”院方出具的结果,与他们之前从名单中了解的信息相差甚远,有人表示不满。
院方解释说,这只是体检的结果,并非鉴定结论,鉴定职业病需要出具劳务关系证明才能进行。医院方面并不承认那份到了导子乡政府的名单是他们传真的。
矛盾迅速激化。他们拉着医院的负责人去了深圳市政府,要求给一个说法。这事惊动了深圳市政府及劳动、卫生等各有关单位。
7月2日,记者在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采访时,遭到拒绝。医院办公室负责人否认那份名单是院方传真给耒阳方面的,但她随后又改口称,这不算是接受采访。
记者却从耒阳方面得知,这份名单确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给耒阳政法委的。
“医院不承认,显然是怕我们当作职业病鉴定结论,这我们表示理解。”患病民工徐新生说,在6月15日当天,聚集的患病群众也确有言行过激之处,但病人心态急切,这也可以理解。
事实上,经过一场风波之后,患病的村民也知道了:检查跟鉴定原来是两回事。
深圳城里的高楼记忆
在深圳市有关部门随后组织的协调中,徐志辉等人看到深圳市领导对于此事的批示,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原则下予以妥善处理。耒阳市也派出由政法委、导子乡、双喜村等相关单位干部组成的工作小组赶赴深圳,与深圳方面交涉。
这些患病的民工提出了要求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诉求。但这显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要认定工伤,须有职业病鉴定书。而做职业病鉴定必须先有确认的劳动关系存在。目前的关键是,劳动关系如何才能得以确认?这相当棘手。
“目前,深圳市劳动局正在逐一调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徐新生说,他们自己也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以证明与那些爆破公司劳动关系的存在。
自己是谁?曾经干过什么?他们需要重新证明。
6月7日,徐瑞宝、徐新生等十来个人,开了两辆车,围绕着深圳城里的高楼大厦,寻找往日的记忆。
“我们想去统计一下,我们到底在深圳做了多少工地,多少高楼大厦的孔桩爆破作业是由我们完成的”,徐新生说,那一天,整整一天,他们在深圳福田、宝安、盐田、龙岗、罗湖等地打着圈圈,结果初步统计有200多个工地,这其中,包括深圳市几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地铁一号线……
“以前,我们只知道埋头苦干,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好好打量这座城市”,徐新生感慨,这么一数下来,才发现,这座城市里每一栋高楼的挺拔而起,都少不了他们这一类风钻民工的辛劳和付出。
在他们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深圳,很小,最漂亮的道路是深南大道,马路都是柏油路。城市里没什么高楼,到处都是山坡、荒地,还有瓦房。
而现在,城市光鲜亮丽、灯红酒绿,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他们虽然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崛起,但现在却经常在市区迷路。
变化太快。如今,他们都已结婚生子,已经成年的孩子,不少人也来到深圳这座城市打工。这座城市,现在需要的是第二代。而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他们,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即便是没有患病,我们也已经很难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7月3日,深圳市召开了全市就业工作会议。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
在王荣看来,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而到城市里打工的人群。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而他们的下一代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家乡,而会成为新的深圳人。
但徐志辉现在会经常告诫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你们还年轻,不要去干这个活,不要去走父辈的老路”。
“我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位老母亲。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我的生命。我要的只是一点公平。”43岁的徐瑞乃声音颤抖,抹了一把鼻涕,在病床上无法坐立。
在外人看来,他目前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愿望只是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一点补偿,去偿还多年来治病所欠下的巨债。
深圳市领导批示要妥善处理,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协调。耒阳市也派出工作小组与深圳方面交涉。
一座寂寥的村庄一个渐行渐远的梦
粉尘之殇
7月9日,正午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在头顶。而我们走进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时,感受到的却是这座村庄的冷清与寂寥。
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半个月前修通的一条水泥马路。阳光直射在地上,一片惨白。
王翠兰、刘秀姬、李秋香等几名妇女正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现在,这些寡妇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她们的丈夫都是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到深圳去打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再被称为“农民工”,不要他们像父辈们一样再回到家乡,而是会成为新的深圳人。可是他们的梦想却被一纸医学证明打破!
或许,悲痛到了极点,过后是平静。
72岁的王翠兰毫无保留地向记者讲述着4个儿子的死。没有流泪。
在中国,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这样的悲剧竟然在她身上发生了4次。“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王翠兰这样解释自己的平静,“每死一个崽,,我也像死过一回”。
1990年前后,王翠兰的5个儿子先后都去了深圳打工,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活:打风钻。在双喜村,很多劳力怀着致富的梦想,来到了特区,打风钻比普通的活要高两三倍的工钱。很多人回到家乡,就开始盘算着建房子,打造一个舒适的“金窝”。乡里、村里一度风传,他们赚了大钱,都发了财。
然而,好景不长,病痛开始折磨这个村庄。
1998年10月22日,王翠兰的第五个儿子徐小伍,病死,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老二徐新春病死,45岁。2007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老大徐白春病死,52岁。王翠兰现在无法向记者证明,她的三个病死的儿子究竟死于何种疾病。但是,村里活着的病人,在他们的CT片上,无一例外出现了肺部不同程度的病变。
“你看,你的肺都烂了。”12组的徐泽志7月7日从衡阳市的医院照CT回家,同村刘阳贵、徐尔平两名被诊断为尘肺或矽肺的病人,指点着徐泽志的胸片,叹息道。这些曾经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同乡,痛恨起南下打风钻时的粉尘。
每死去一个,这个村里就会增加一名寡妇。”自从丈夫死后,55岁的刘秀姬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丈夫徐龙古于1990年出去打工,1998年发病,2006年九月初六去世。在打工期间,徐龙古每年能赚一两万块钱,打工10年赚了十多万元,但为了治病却花了30万。
“房子也没盖,至今还有几万块钱的债没还。”如今的家,只有四堵墙壁,里面空空如也。
而在双喜村,这样的人间悲剧,一再上演。
更多的男人被检出“肺部阴影”,有的被明确诊断为尘肺或者矽肺。他们正值壮年,却已无法参加体力劳动,“我们已经像个废人了”、“我自己的病治是治不好了。”徐瑞宝一家子最多的时候有7人在深圳打风钻。这其中包括哥哥徐瑞乃、两个妻哥谷运成和谷桂成、侄子徐小斌、姐夫王从成、侄女婿刘韧,他们打风钻时间长的有10年,短的也有4-5年。7人中,目前只有谷桂成没有查出“肺部阴影”。
41岁的徐瑞宝是村里最早一批前往深圳的风钻工。现在,他经常想起自己刚到深圳时的惆怅。1989年9月份初三开学的时候,他在深圳福田区黄木岗干活刚满一个月,但想起自己因为家庭贫困放弃了学业,心里一阵难过。“那时候,我们种着七八分田,两三分地,几乎没有收入。”南下打工是徐瑞宝和他的老乡们当时不可回避的现实。
那是他们试图改变命运的捷径。而命运却是如此残酷,残酷得让人还来不及承受这些粉尘之重。
[记者手记]
活着是一种负担
继续活着是一种责任
10年前,他们前往深圳,带着致富的梦想。
10年后,他们万念俱灰,只求自己最后的努力下,能获得赔偿,家人能还清所欠的债务。
然后,他们在家乡的小屋里静静地等待死亡。
在采访过程中,我没有见到他们流下一滴眼泪。也许,眼泪早在几年前,就已流干。现在,即便是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他们考虑到的却是家里的孩子能否有钱读书,妻子是否以后能够找到好男人,父母是否会得到好的照顾。有些人甚至在悄悄地积攒安眠药,等自己实在无法忍受病情的时候,自己结束生命……
当徐瑞乃带着呼吸器告诉我:“我想回家,我不想呆在深圳医院里了。家乡的空气好,这会让我在后面的日子里过得舒服点!”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活着,也许对现在的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负担了!
可是,他们的眼神却又告诉我,继续活着,好好地走完这些剩下的日子,对家人而言,也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