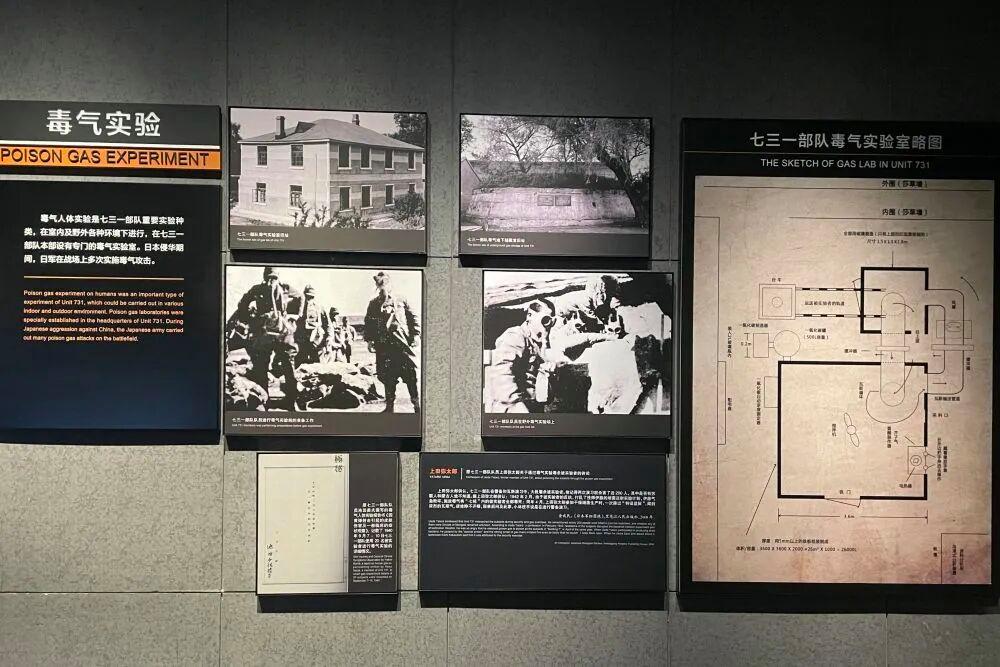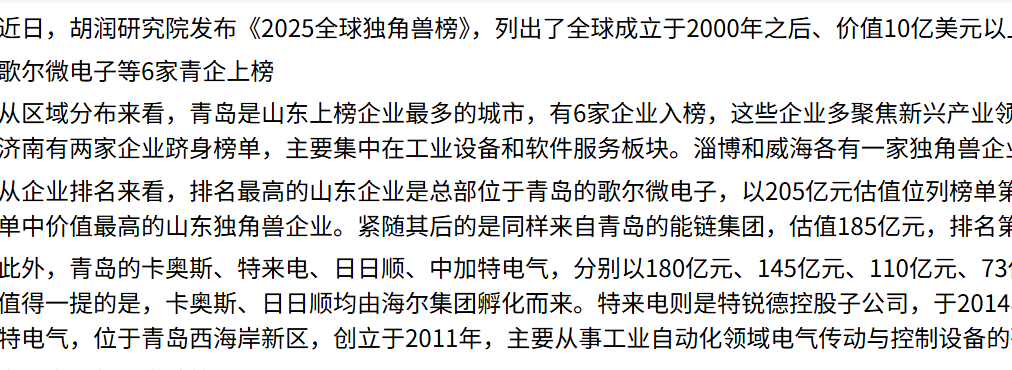文 | 新京报记者韩雪枫 实习生王昱倩 编辑 | 苏晓明
李云的出租屋位于浙江温岭市一个城中村,街道上到处散发着油炸食品的味道,村里住着大量外来务工者。李云的屋子很小,只有10多平米,里面只有4张高低床。
她1米55的身高,扎着高高的马尾,戴着蓝色口罩,说起话来总是下意识的低头,生怕别人注意到她口罩后面的鼻子。
在一年前的一次争吵后,李云的鼻子被丈夫割掉了。
而在此之前的8年时间内,丈夫曾一巴掌打到她鼻子流血,拿刀架在她脖子上,侮辱她,威胁她,甚至扼杀了她的孩子。
她从不反抗,选择隐忍和逃避。为了躲避丈夫毒打,2014年7月,她从湖南吉首逃到浙江温岭,找了一份酒店前台接待的工作,决心跟过去的生活告别。
像无数次被家暴后一样,李云选择原谅丈夫,她把丈夫带到温岭。这成为她这一生最后悔的决定。
在中国,李云是家庭暴力中受害者的缩影。去年年底,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透露,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25%的女性正在或曾经遭受家暴。
他们在经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还要面对周遭的冷遇,社会救助体系的匮乏和有法难依的尴尬。
“婚姻就是两人一起赚钱,生儿孕女”
李云1986年出生在湖北恩施咸丰县农村,土家族。父母都是农民,她有一个妹妹,家里经济拮据。
16岁时,李云从初中辍学。她先是在湖南龙山县一家饭馆当服务员,两年后去了宁波一家家电厂做工人;2006年前后,她进入重庆一家纤维加工厂做女工。
“她性格像男孩子,跟谁都能玩到一起,我们都叫她‘男人婆’。”李云曾经的工友范玲对剥洋葱说,李云五官清秀,高鼻梁,大眼睛,笑起来很迷人。
在即将20岁时,李云想结束这种居无定所的日子。家里催婚的电话也多了起来。“我们山里人,结婚都挺早的,很多人十五、六岁就成家,等到了法定年龄再领证。”
“我该找个人结婚了。”李云说,她想象中的婚姻简单又美好:“两个人一起努力赚钱,生儿育女,过好日子。”
2007年10月,她在湖南打工时认识的工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龙党宝,比李云大11岁,两人加了QQ。李云说,她不在乎年龄,只要对她好就行。
龙党宝是湖南湘西花垣县张刀村人,全村200多户,有一大半姓龙。村子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是一条缠绕在半山间的水泥路,车迹罕至。
花垣县距离李云的家有近300公里路程,两地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在政府文件中,花垣、咸丰和周边的一些县市,被称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3年,有驴友在花垣县徒步,拍下了张刀村寨子。图片来自网络。
相较李云四处打工居无定所,龙党宝则一直待在家乡。他的堂哥龙金成说,龙党宝12岁时,父亲去世,留下龙堂宝、母亲以及三个姐姐、两个妹妹。龙党宝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姐姐挣钱供他读书。
“17岁时,我们一起从高中辍学,每天搭伙出去做农活,变成各自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龙金成回忆,作为贫困山区的青年,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事。
务农期间,龙党宝有了第一任妻子,两人结婚并生下3个女儿。
龙金成向剥洋葱介绍,第三个女儿出生后,龙党宝和前妻关系逐渐恶化,最后离婚。
在通过朋友介绍互相认识之前,李云和龙党宝两人的生活像两条平行线,那次偶然相识,让他们的命运彻底绑在一起。
“他像一颗炸弹,随时可能换回一顿拳头”
“不要饿着了,我会心疼。”刚刚认识时,龙党宝经常在网上对李云嘘寒问暖。对着电脑屏幕,李云都能笑出声来。她感觉“找到了依靠”。
网聊一个月后,龙党宝对她说,他愿意照顾她。李云毫不犹豫地辞掉重庆纤维加工厂的工作,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龙党宝的家乡。
在火车站见到龙党宝,1米8的个子,身材魁梧,体重有180斤,身材娇小的李云顿时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但安全感很快消失,她发现,这个男人并不像在虚拟世界中那样美好。
他欺骗了她,龙党宝告诉李云自己是做生意的,其实他开黑车为生;他隐瞒了自己有过一段婚姻和有3个女儿的事实。
他脾气暴躁。因为心情不好,开车时,龙党宝专门碾压死了路边一条狗。
他还打人。在他们见面后的第二个月,龙党宝第一次打她。
李云的一个姐妹从外地到湖南看她,李云出去陪朋友吃饭。龙党宝很不高兴,两人争执了几句,龙党宝打了她一巴掌,“啪”的一声,血从她鼻子中流了出来。
对于男人打女人,李云很震惊,“在我家里,爸爸从没对妈妈动过手。” 她对“家暴”这个词一无所知,把丈夫打人的行为定义为夫妻间吵架。
4月22日,李云在温州一家整形医院,她的口罩比一般人拉得高些。新京报记者韩雪枫 摄
李云的姐妹劝她早点分手。但李云原谅了他。“他后来向我承认错误,说他是我未来老公,比朋友更重要,我应该陪他。”听到这些话,李云觉得龙党宝是在乎她,“心里还有一些高兴”。
不过,第二次暴力很快到来。那是4个多月后,龙党宝已经听从李云的建议,不再开黑车,去了老家的矿山工作。
那一天,两人在屋内看VCD,李云觉得片子不好看想换一个,龙党宝突然冲了过来,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摁在墙上,李云“喘不过气来”。
此时,她已经怀孕3个月,为了肚里的孩子,她再次隐忍。
李云对剥洋葱说,在她怀孕期间,丈夫还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暧昧。她质问丈夫,“难道我不如别人好看吗?”丈夫回答:“你就鼻子好看。”
2008年12月,女儿出生。此后,丈夫对她施暴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刚开始几个月动一次手,后来两个星期一小打,两三个月一大打。”
李云说,“他像一个炸弹。”有时候仅仅只是说话声音大一点,都有可能换回一顿拳头。”
2010年,李云再次怀孕,由于第一胎是女儿,龙党宝的姐姐带她去卫生院做了胎儿性别检查。检查结果是女孩,于是丈夫找了熟人关系,把她带到花垣县人民医院进行引产。当时,李云怀孕7个月。
“为了这件事,我天天晚上流泪,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生儿子的工具。”李云说,她想离婚,但看看身边的女儿,忍了。
“他每次动手后,都向我道歉,说打人时脑袋是空白的。”李云说,丈夫还会写下再不打人的保证书,这些年,“保证书堆起来可以当枕头。”
但在外面,龙党宝总是伪装成对李云很好的样子。“他看起来对李云百依百顺,有时候我们一起打牌,小李过来叫他,他就乖乖地走了。”龙金成对剥洋葱说。
“婆婆说,她年轻时也经常挨打”
2011年,李云曾向丈夫提出离婚。丈夫暴怒,并威胁她,如果离婚就报复她的家人,李云十分害怕,再也不敢提这两个字。
反家暴专家、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介绍,在家庭暴力中,受害人往往不能主动从家庭暴力中逃离,因为他们陷入“受虐妇女综合征”。
李莹最近干预的一个案子中,施暴者与受害者都是高校教授,但在十多年的家暴中,受害人已经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丈夫吓唬她,如果报警就杀掉她和她的家人,我了解后可以肯定,她丈夫这种视地位如生命的人,不可能为了她自毁前途。”但受害人却深深相信丈夫的话。
李云曾向婆婆哭诉,但婆婆告诉她:“自己年轻时也经常挨丈夫的打”。
李云想过报警,但又觉得警察不会管家务事,她始终没能迈出这一步。
据全国妇联调查的数据,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
浙江温岭市某城中村,李云的出租屋位于4楼。去年,她的丈夫在这里割掉了她的鼻子,并扔到窗外。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摄
而在现实的众多家暴案例中,当警察真正介入并带走丈夫时,很多妻子是不同意的。
“去年有人报案,说邻居丈夫殴打妻子,我们出警,把丈夫带到派出所调查。”湖北一派出所的教导员告诉剥洋葱,“没过多久,女子带着婆婆就到所里又哭又闹,一口咬定身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我们只能放人。”
为人熟知的家暴受害者通过警方抗争成功的案例,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事件。
2011年,李阳家暴事件曝光。他的妻子向警方报案,在警方协调下,李阳在派出所签下了承诺书,保证不再使用暴力,并接受心理咨询,之后在微博上向李金道歉。
日后李金起诉李阳,这些都成为了法庭上的有力证据。
但现实生活中,像李金一样勇敢坚强、有法律意识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受害者太少了。
“我有钱,我可以回美国,可她们呢?”李金说的她们正是像李云这样遭受家暴而默默承受的女性。
倍感无力的李云打电话向父亲求助。父亲身上藏了把刀,来到他们家。他想,如果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就跟女婿拼命。
可女婿龙党宝认错态度非常好,李云父亲心软了,觉得夫妻有矛盾也正常,只能告诫他们“家和万事兴”。
逃出湘西
2011年,李云怀上了儿子。龙党宝很高兴,从矿山上回村子里盖了自己的房子。房子盖好了,龙党宝身体却不行了,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和哮喘,之前挣的钱都用在治病上。
生完孩子的2012年,李云和龙党宝到了湘西州府吉首。他们买了一辆车,给宾馆送纸巾。但只做了几个月,由于生意不好,车子也卖掉了。
宾馆送纸巾的生意失败后,为了养家,李云做了两份工作:早上摆摊,卖些油炸的早点,下午就去服装店做服务员。龙党宝在家里带孩子。
“她老公三天两头来闹事。”李云在服装店的老板说,她明显感觉到龙党宝并不愿意妻子在外工作。
“他这人脾气不好。”李云向老板解释。而这几乎是李云在外面对龙党宝最严厉的指责了。
李云说,龙党宝认为靠女人上班挣钱脸上没面子,“他觉得我让他变成了吃软饭的。”
龙党宝开始酗酒,并经常跟李云伸手要钱。
李云出具的鉴定书显示伤残达重伤二级。受访者供图。
2014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晚上,龙党宝向李云要2000 元钱。李云拒绝了。
“在大街上,他扯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电线杆上撞——砰,砰,砰。我倒在地上,他用脚不停地踹我、踩我。”李云向剥洋葱回忆,最后龙党宝把她扛回家,她十几天下不了床。
那些天,丈夫每天悉心给她换药,并且一次又一次向她道歉。
不过李云已经彻底不再相信。她不敢离婚,不知道向谁求助,只剩下一条路——“逃”。
国内首个民间女性公益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刘凤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接到过很多家暴求助,她能告诉她们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带上钱,逃到安全的地方。”
2014年7月,她以为女儿找学校为由,离开了吉首,乘坐长途汽车辗转来到浙江温岭,投奔在那打工的妹妹。
“孩子读书了,不会像我这样了吧”
李云带着女儿逃到温岭后,找到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她换了手机号,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不过,丈夫一直在QQ上给她留言。“他说对不起我,让我原谅,说儿子想我了。”李云和剥洋葱说,儿子是她最大的弱点。
2015年春节,李云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她回湖北老家过年,年后去了一趟花垣县,原谅了龙党宝,并将他带到温岭。
来到温岭后,丈夫工作没几天就辞了,接下来整天喝酒,并不停劝李云回老家。李云不回,丈夫又开始家暴。
“出事前一周,我看到她的额头有淤青。”李云的同事刘艳(化名)说,但李云并没有说发生了什么,还拜托刘艳帮丈夫找一份工作。
2015年3月30日凌晨,从酒店下班回到家中。喝了酒的龙党宝又提起回老家的事,他们之间再次发生争吵。
“我躺在床上睡觉背对着他,他用刮眉毛的刀片割了一下我鼻子,鲜血从鼻子上涌了出来。”李云说,丈夫一只手用毛巾勒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猛地把尚未完全断裂的鼻子撕扯下来,扔到了窗外。
“你鼻子最好看,我就让你没鼻子。”龙党宝说。
而龙党宝曾向堂哥龙金成说,“他当时在刮胡子,小李有三台手机,不停有短信在响。他怀疑她出轨,就去夺手机看短信内容,争执过程中,误伤了她的鼻子。”
4月3日,李云的父亲从湖北赶到了温岭,向派出所报案。
在医院待了5天,龙党宝的姐姐过来,给了李云5万元钱,并以回家筹钱治病为由带弟弟回了家。
事发后,龙党宝一直在QQ上请求李云原谅。
4月9日,公安部门为李云做了伤情鉴定,李云的鼻子被确定为重伤二级。法医鉴定结果为:鼻子缺失约70%,仅剩少许鼻根及两侧鼻翼残存。
据温岭警方消息,龙党宝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列为刑拘在逃对象,公安部门已经对其上网通缉。
“他一直在QQ上向我留言,说他错了。”记者注意到,龙党宝留言的时间跨度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但从去年6月开始,龙党宝已经被网上通缉。
“出了这个事之后,我从网上搜到了温岭妇联的电话,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们说我不是本地人,让我找家里的妇联;我找了花垣县妇联,但他们让我找事发地的妇联。”李云感到十分无力。
温岭市妇联拒绝了采访请求。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李莹说,“《反家暴法》没有规定必须是户籍所在地的妇联才能管,现在许多人不在户籍所在地工作,受害人向实际居住地的妇联求助后,妇联应当干预。”
鼻子被割后,李云常常做噩梦,她梦到丈夫提着一把刀追她。“我拼命跑,但跑不出去,醒来了就哭。”
李云觉得,自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除了恢复容貌,她最大的愿望是让8岁的女儿上学。但高额的治疗费和外地户籍的限制,让她两个愿望遥遥无期。
李云从网上买了几本小学课本,每天在病房里给女儿上课。她的病房挨着一所小学的操场,每当运动场里音乐响起,她总幻想女儿也出现在那里。
“孩子读了书,以后不会像我这样了吧。”李云和剥洋葱说。
(为保护受害者隐私,文中李云为化名)